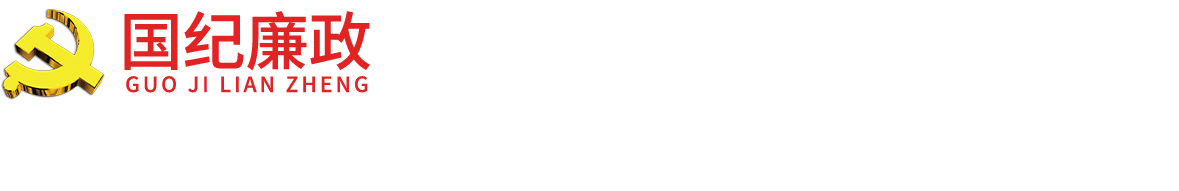美丽中国丨绿之春城
一
飞机降落在宜春明月山机场时,我刚刚睁开朦胧的双眼。舷窗外的绿意,如同久未重逢的朋友,要给我一个热烈、深情的拥抱。
南方的中秋时节,到底还是有些热,但已不似伏天那样热浪灼人,让人在街上只能跳房子式行走。阳光洒在头顶,只需用手曲成一座小山状,遮一遮,便不觉刺眼。
我抬头望了望机场周边的小山,它们是指示我回到家乡的向导,和缓的曲线铺陈在大地之上,再用鲜艳欲滴的绿色一笔一笔填在这曲线与地平线构成的空间中。
“是不是觉得空气都更甜了?”母亲在停车场见到我时如此问,我微笑着点了点头。机场其实离市区并不远,而且随着城区面积的扩张,机场几乎连郊区也不算了。我一个人打车回家也很方便,但母亲和父亲却坚持要开车来机场接我。
“你一年就回家两次,我们不来接,谁来接?”我坐到副驾的位置后,母亲转坐到后排位置上,对我的“体贴”颇有些嗔怪。窗外的青山,如一幅卷轴画一样,一些景致在车尾处收束不见,而一些新的景致在车头又展露出来,我倒要看看这幅卷轴画有多长。
忽然想起了一句古诗,“一水护田将绿绕,两山排闼送青来”,这是老乡王安石的《书湖阴先生壁》。以前读此诗,总觉“排闼”二字不甚好解,现在都解了——青山撞开了我的门,不请自来,它就这样热情填满每一个人的视野,让观者的瞳孔中倒映出青山的婀娜身姿。
毫无来由的,天上飘起了小雨。雨很快就停了,而我的思绪却停在了小学时的一段往事。那大概是四年级吧,我误打误撞报名参加了合唱团与鼓号队,所有排练的曲目我都忘记了,只记住了那首《春雨蒙蒙地下》。二十年过去了,我竟还记得那旋律与歌词:“春雨蒙蒙地下,唰唰唰唰,唰唰唰唰,绿了河边的杨柳,红了村前的杏花。”
有一回,也许是个周末,合唱团的成员在阶梯教室中排练《春雨蒙蒙地下》,外边的天光,从明媚变得晦暗,春雨真的蒙蒙下起来了。教室外,本是一片茂密的树林,那些高大的樟树,不知经历了多少年月,看过多少世事沧桑,对于我们这些懵懂的小孩,树就是这世间无言的老者。
春雨浇灌在老者的身上,让老者披上了一层光鲜的绿衣,老者再度年轻起来。雨滴在绿叶上旋转了一圈后,从叶脉滴落大地时,它已然成为了一颗翡翠。在教室中唱歌的我,只想扔下写满音符的书,跑去春雨中大玩一番,去拣拾那美丽的翡翠,或者直接让身体成为装藏翡翠的容器。
雨声越来越大,终于盖过了我们的合唱声,在老师的指挥下,我们停了下来,人声在此时竟是如此无力,我们专心看窗外的那雨、那树、那令人心旷神怡的绿。我开始认为,是我们的歌声把雨从天上唱了下来。
可不要小看了音乐的力量。许多年后,当我来到甲秀天下的桂林山水,骑行在遇龙河畔时,耳机中传来刘三姐的动人歌声——“多谢了,多谢四方众乡亲,我今没有好茶饭,只有山歌敬亲人。莫讲穷,山歌能把海填平,上天能赶乌云走,下地能催五谷生。”倘若山歌能把海填平,能把乌云赶走,能催熟五谷,那么也一定能让一场蒙蒙春雨从天际飘落大地。
二
这回中秋回故乡,赶上表弟的婚礼。我与表弟在同一个城市念书,毕业之后,他回了故乡,我成了北漂。每年的相见只限于春节与国庆两个时间稍微长些的假期。因为表弟的婚礼,一些阔别多年的亲友回到故乡,大家归乡情不怯,话题一个接一个,就连新人的答谢酒几乎都要错过。
散席后,母亲说附近新开了一座公园,名唤灵泉池,可以去看看。母亲拉着我的手,就如儿时春游一样,大手拉着小手,只是我的手大了,母亲的手小了。
我们钻入了一片绿中,喧嚣被挡在了绿帘之外。绿竹猗猗,王维独坐幽篁里,一人弹琴复长啸,只有明月来相照,他的寂寞融化在竹林中,使竹都带着几分无端的寂寞。公园里的竹林,却成了众人乘凉、嬉戏的好去处,许是沾染了人的气息,这片竹林也通了人性。就在我们将到达灵泉池时,风扫过竹林,发出哗哗的声响,好似在说欢迎、欢迎,你终于来了。
灵泉池并不在我的记忆中,但曾是母亲生活的一部分。母亲小时候,自来水还不普及,用水就得来灵泉池挑。眼前为栏杆圈起来的灵泉池,已非旧时模样。“这么说,你会用扁担?”我问道。母亲点了点头。这是我不曾知道的母亲的过去,也是我不曾知道的这座城市的过去。
自打我有记忆起,灵泉池公园所在的地方就是一片高楼大厦,近年来,老城区开始更新,高楼不见了,一个复兴古城的项目,推动了灵泉池公园的建设。“你快来看,原来我们城市的名字来源于灵泉池”,母亲指着一块字牌对我说。
西汉初年建立豫章郡,郡辖十八古县,这是江西最早成立的一批县,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。这十八古县中,如今最知名的也许是海昏县,因为海昏侯汉墓发现的文物令人极感震撼。宜春也是十八古县之一,其得名源于城西美泉,此泉“夏冷冬暖,莹媚如春,饮之宜人”。宜春之名一直用到了现在,过去曾是县名、侯国名,如今是市名。
在自来水普及之前的时代,城中的古井是人们的主要水源,有人的地方,便有故事,便有文化。要不怎会有“凡有井水饮处,即能歌柳词”的说法,柳永的词,便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口耳相传,成为市井流行文化。
我想起了一位宜春本地的诗人,他在唐诗史上也很有些名气。郑谷,诗僧齐己的“一字之师”。齐己有一首《早梅》诗,颔联原为“前村深雪里,昨夜数枝开”,他拿此诗求教于郑谷,郑谷只提了一条建议,将“数枝开”改为“一枝开”,数枝算不得早,一枝才是早,是先声夺人。
郑谷本人以一首《鹧鸪》诗闻名诗坛,时人唤他“郑鹧鸪”。诗曰:“暖戏烟芜锦翼齐,品流应得近山鸡。雨昏青草湖边过,花落黄陵庙里啼。游子乍闻征袖湿,佳人才唱翠眉低。相呼相应湘江阔,苦竹丛深日向西。”游子闻鹧鸪声,不禁泪湿双袖。
旧城改造前,我家就住在鹧鸪巷,巷口有一孔大水井,在家家户户都通了自来水后,仍是热闹的所在。母亲总是提醒我,在井边行走时要注意那些湿滑的青苔。卑微的青苔,从砖缝中寻出一片出头天,在经历他人未知的无穷挣扎后,就这样以微小的但却是明确无误的绿意,宣告一场生命的旅行的降临。
我知道在一个新春,旅居长安的郑谷,试图透过一片青苔去寻找家的感觉,在《中年》这首诗中,他写道:“苔色满墙寻故第,雨声一夜忆春田。”我相信记忆是有颜色的,并不会随时间的流逝而逐渐黯淡,倒有可能经过我们的反复上色而越发鲜亮,对于郑谷,故乡是绿色的,是湿润的,对于我亦是如此。
三
在灵泉池公园旁的一条小路上,我和母亲聊起了以前住的地方,豁然发现了唐五代时期的古城墙,这是近年来宜春的一项重要考古发现。说不定郑谷果真曾经住在那一带,要不然怎会有鹧鸪巷的名字呢。耳边逐渐响起了汩汩的流水声,原来我们竟不知不觉走到了秀江畔。
秀江是赣江的一级支流袁河在宜春城区的一段,是宜春人的母亲河。记得小学时写秀江的作文,十篇有九篇将秀江比喻为一条绿丝绦。虽然俗气了些,却很形象。秀江穿城而过,将城市分成了南北两区,南区是老城区,北区更新。这条自西向东流动的绿丝绦,仍如我儿时记忆中的一样碧绿。
宜春话中有一个十分形象的词来表达水之清澈——“滚清滚清”,清字发后鼻音,便有一种特别强调清的意味,水因流动不止而汰除了杂质,留下一片纯净,倒映出万丈碧绿。
回到家中,父母同我商量接下来几天去哪里玩。这几年,我们利用假期开车去周边旅行,已去看了高安的元青花,攀登了铜鼓的天柱峰,观赏了万载古城的绚烂烟花。
“要不要去明月山逛逛?”母亲问我。自高中毕业旅行后,我再没有去过明月山,但我总觉得那就是昨天的事,云谷飞瀑溅到手臂上的小水珠,好像一分钟前才干涸。
正当我犹豫之际,父亲说:“在家里就能看到明月山。”我家住在城南的一个小山坡上,视野极好,从书房向外望去,城市霓虹闪烁,人间烟火气十足;从客厅向外望去,城市南边的脉脉青山中,必有明月山。接过父亲递来的望远镜,在父亲的指点下,我尝试搜寻明月山的踪迹。
我脱口而出四个字——远山含黛。远山不再是那鲜艳欲滴的绿,它离得更远,却更大方,更显媚态。在铺开的画卷中,只是用淡淡的水墨浅浅勾勒出一组线条,大片的留白让这水墨更富禅意。禅是不可言说的,山水也是不可言说的,说出便陷入到语言的窠臼中,就失却了本意,只有心领神会这山水中的清音才是正途。
我想到了一个旅行的好去处。“我们去仰山吧。”仰山离明月山不远,曾是郑谷隐居之所,是中国禅宗五家七宗之一的沩仰宗发源地,那位郑谷的学生齐己就是在大沩山中长大的,很有可能,是他到仰山来与郑谷见面论及《早梅》之诗。
我早已听闻仰山栖隐禅寺的大名,那是一座为青山环抱的寺。中国的名山佳水总是与儒释道相随相生,一方山水滋养了一方文化,我须看看仰山之形势,问问沩仰宗何为“方圆默契”。
我望着窗外的青山,思绪不知飘到何处,直到饭菜的香气扑来。不知郑谷隐居仰山时,可曾贪恋饭菜的香气。到底尘世还是迷人的,到底青山还是可爱的,对于两者都不能割舍的人而言,城市山林是最理想的家园。
明代大书画家文徵明深谙此道,他曾为如今已消失的拙政园中若墅堂题诗:“会心何必在郊坰,近圃分明见远情。流水断桥春草色,槿篱茅屋午鸡声。绝怜人境无车马,信有山林在市城。不负昔贤高隐地,手携书卷课童耕。”
好一个“信有山林在市城”。若墅已没,而眼前的青山尚在;拙政虽远,而绿意总萦绕在心头。(文若水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