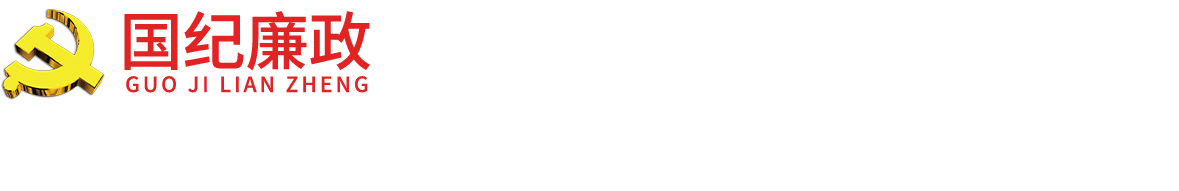青史斑斑 | 梅花岭上慰忠魂
江苏扬州史可法纪念馆中的祠堂,对联为“一代兴亡关气数,千秋庙貌傍江山”,系清代扬州知府谢蕴山所撰。关于这副对联,还有一个颇具深意的传说,记载于袁枚的《子不语》中。谢蕴山在梦中见到史可法,谢蕴山问其是否知道为他修葺祠墓之举,史可法表示知道,认为此非俗吏所能为,并告诫他为官“不患无位,患所以立”,为官者要担心的是自己的作为是否与职位相称。谢蕴山又问祠堂尚缺一副对联,史可法思考片刻后,咏出了上述对联。
“终古衣冠留葬处,万流瞻仰慰忠魂。”春和景明的时节,扬州城外,梅花岭畔的史公祠,前来瞻仰明末爱国将领史可法的人络绎不绝。从1644年到扬州督师,到1645年壮烈殉国,史可法在扬州的时间不足一年,却深为扬州人怀念。回顾其壮烈的人生历程背后,读与写是不容忽视的重要维度。
勤学苦读,兼有文武之才
自古文武不分途。赫赫有名的民族英雄史可法,本是一介书生。从有迹可循的零珠碎玉中,我们对史可法的读与写仍可窥见一斑。
史可法生于一个书香之家,其祖父曾经中举。他年幼时在乡间读书,就以“兼有文武才”而出名。因为苦读,也因为才华出众,史可法很早就给顺天府学政左光斗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左光斗,安庆府桐城县人,其地文风兴盛、名家辈出,他于万历三十五年(1607年)进士及第,“素擅文名”,后来因弹劾魏忠贤而下狱,死于狱中。
方苞《左忠毅公逸事》记载,一日,左光斗视学京畿,风雪严寒,晚上入一座古寺,不料见到廊屋里一个年轻人“伏案卧”,这正是游学郡庠的史可法。左光斗拿起案旁墨迹未干的文稿,“即解貂覆生,为掩户”,并“叩之寺僧”。方苞果然是桐城派大家,十二个字,一连串的动作,既写出了左光斗对寒门后生的爱护,更衬托出史可法文采斐然。虽然史可法的这篇文稿内容已无法得知,但能让左光斗看重,足以说明史可法的文章大有可观。
史书记载,天启元年(1621年),20岁的史可法,被拔为秀才第一名,主考官正是左光斗。考中秀才后,史可法更加勤奋,后来回忆这段日子,他深有感慨地说,自己做秀才时,一月仅得七夜整眠。左光斗对其厚爱有加,甚至将其接到家中居住,与家中子弟一同读书。左公闲余时,“悬榻以俟,相与抵掌时事,辨论古今”。左光斗是将史可法作为衣钵传人来培养的,“他日继吾志事,惟此生耳”。与左光斗相处日久,史可法学业精进:天启七年(1627年),26岁,中举人;崇祯元年(1628年),27岁,登进士第。这一年,考中进士的共353人,史可法三甲第26名,赐同进士出身。
中进士后不久,史可法任西安府推官,从此走上仕途,直到弘光元年(1645年),他44岁以身殉国。其间,崇祯十二年(1639年)到崇祯十四年(1641年),因为父亲去世,他按照传统礼法的要求,回家丁忧守孝,“闭户读书,茹菽饮水”,“复理经史旧业”,可以想见其如饥似渴的读书模样。史可法家居期间,“碎金带自给”,因为家中人多花费大,史可法不得已将朝廷赐予的金腰带上的金片典当换钱。他虽然身居高位,但绝少应酬,难得长期在家,他的时间多用在读书上。
除了守孝的这几年,其余时间,正如其幕僚王之桢在《跋史师相乞闲咏叙》中说,“余从师相在维扬幕府,时军务旁午,绝不见师相理古人文字。”军政交错,事务繁杂,史可法实在无暇读书,这是他的无奈。不过,王之桢帮他打理行装,却发现他行囊中仍携带了一本欧阳修编撰的《新五代史》。有书相伴,方能心安,这是书生本色。
爱读经史,醉心于宋代文豪欧阳修的文章
从上述“复理经史旧业”可知,史可法丁忧在家以及此前读书,均以经史为主。他撰写过一副对联:“斗酒纵观廿一史,炉香静对十三经。”说得上是他对自己读书的自注。
参加科举考试,必须读经。明代八股取士,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做题目,阐述其中的义理,措词要用古人语气,文章格式不能跳脱规定,即所谓代圣贤立言。如此易固步自封、思维僵化。四书五经,毕竟是圣贤智慧的结晶,若只为功利而来,自然收获颇浅,若为修齐治平而来,其中有浩大的境界。
史可法钻研经书的成就,犹未可知,不过从《史可法集》(清张纯修编辑,罗振常校补)中的两篇文章而言,史可法对“仁”的理解,能从自我出发,一语中的。一篇是对《论语·述而》中一段话的阐述,这段话是孔子与学生公西华的对话。子曰:“若圣与仁,则吾岂敢。抑为之不厌,诲人不倦,则可谓云尔已矣。”公西华曰:“正唯弟子不能学也。”孔子不敢自居圣与仁,只是孜孜不倦地追求圣与仁的境界。史可法则由此提出,“天下事不自我操之,则四海无功;不自我深之,则百年无学。”另一篇诠释的是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的“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”,史可法认为“心乎天下者,已于畴咨之内,偕万灵之性命而嘘,则施济之奇,不动声色,混乎生机之浩荡而已矣。”由这些只言片语,我们能看到他一生蹈仁履义的坚定。
史可法读书,“所尤醉心者,《欧阳文忠公全集》也。”史可法爱读欧阳修,这固然因为欧阳修的道德文章堪为师表。欧阳修既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支持者,也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,他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,其散文创作的成就与其古文理论相得益彰,开创一代文风。
史可法醉心欧阳修,与其师左光斗的影响也不无关系。左光斗的文章奏议、诗词章句气势雄浑,针砭时弊,鼓舞人心,是桐城派的先导,而桐城古文运动,与唐宋古文运动一脉相承。桐城派中,方苞的“雅洁”与欧阳修的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实质是一个意思,刘大櫆的“因声求气”简直是欧阳修《秋声赋》的化用,姚鼐的“义理、考据、词章”与欧阳修的明道、致用、事信、言文如出一辙,桐城派“道统自任”与欧阳修的“文道合一”“文以明道”大同小异。史可法的文章,“能以简古胜”,这与欧阳修、左光斗以至后来桐城派的风格是一个脉络。
戎马倥偬,史可法将欧阳修的《新五代史》带在身边,不是偶然的。五代是一个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,而宗庙朝廷人鬼皆失其序”的“乱世”,这与明末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何其相似。人的心境往往对选择读什么书有影响。《新五代史》充盈着一种浓厚的悲剧气氛和强烈的抒情性,它或许暗含着史可法对明朝命运回天无力的无奈。但前途虽然坎坷,史可法还是抱着一线希望,希望知己知彼,力挽狂澜。这是他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”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的书生意气。
文章蕴家国之思,存浩然正气
史可法留下的作品并不多。他“从未尝以文字与章句之士争高下”,他写的多是实用性文章,少数的几首诗,也有感而发,从不无病呻吟;再者,扬州城破,“一切化为灰烬”,身已许国,遑论文章。
尽管如此,史可法撰文,却令人神往。据其幕僚王之桢亲眼所见,“幕中无一简点文字者,一切奏揭书启之类,日于漕政暇,应发数十通,口授数敏书吏,使书之。比脱稿,皆醇鬯淹雅,曲尽机宜。又走笔判押,运腕如飞,字字皆《十七帖》(王羲之一系列名帖的总称,因第一帖以十七开头故名)也。”史可法的文稿,坚持自己构思,不用幕僚代笔,文如泉涌,令人惊叹,这当然得益于他的苦读善读,“于古人书无不领其要旨”。
史可法的奏疏现存36篇,或向朝廷谢恩,或请辞朝廷赏赐,大多数都是就军政要务向朝廷建议。1644年农历八月,他接连向朝廷上疏两次,一是《论人才疏》,一是《请进取疏》。这一年,李自成兵破京城,崇祯自缢煤山;这一年,清军入关,铁骑横扫;这一年,福王即位,南明飘摇;这一年;战乱不已,民不聊生。史可法面对内忧外患,心急如焚。一方面,朝廷内讨巧的多,做实事的少,“此推彼卸,姑付庸人,倏用倏更,有同儿戏”,“举诸臣精神力量,尽用之做官,曾无为国家实实筹兵饷者”;另一方面,福王朱由崧即位后,苟且偷安,贪图安逸,史可法预见“进取不锐,则守御必不坚”,果然不出其所料,南明很快被灭。史可法的奏议,不仅观点鲜明、分析精准,且切中时弊、要言不烦,在文采上,多用排偶,条理精密,文笔流畅,气势充沛,是以时人甚至将之与唐代政治家陆贽的政论文章相提并论。
史可法现存书牍中,最有名的莫过于《复摄政王》。当时清军兵强马壮,来势汹汹,南明势单力薄,人心丧失,史可法这封写给多尔衮的信,既针锋相对,又绵里藏针,既措辞委婉,又心念坚决,“庙堂之上,和衷体国;介胄之士,饮泣枕戈;忠义民兵,愿为国死”,表明自己为国捐躯的决心。信中五次提及《春秋》,非但毫无啰嗦之感,反而觉得有理有利有节。这其实也是史可法读书的现实运用。《春秋》乃是一部申明大义的经典,古人在国家危难之时,每以《春秋》来辨明是非、鼓舞斗志。
史可法存世诗仅7首。其《燕子矶口占》云:“来家不面母,咫尺犹千里。矶头洒清泪,滴滴沉江底。”有家不能回,有母不能见,清泪原不轻,能沉入江底,叙事饱含抒情,那种对母亲的思念和歉疚之情,隐在其中,既未明说而又呼之欲出。仅凭此,史可法足可跻身明末一流诗人行列。
《燕子矶口占》应当写于1645年。这年农历四月,扬州城破,史可法被执至扬州城南门,面对投降的建议,他“大骂而死”,英勇就义。史可法的遗体不知下落,后人将其生前穿过的袍子、帽、靴和用过的笏板,遵其生前的意愿,埋葬在梅花岭上。
站在梅花岭上,遥想史可法的忠烈事迹,遥想史可法的读书撰述,我们看到的是对儒家修齐治平理想的勇毅笃行,是天地无私的浩然正气。(赵建国)